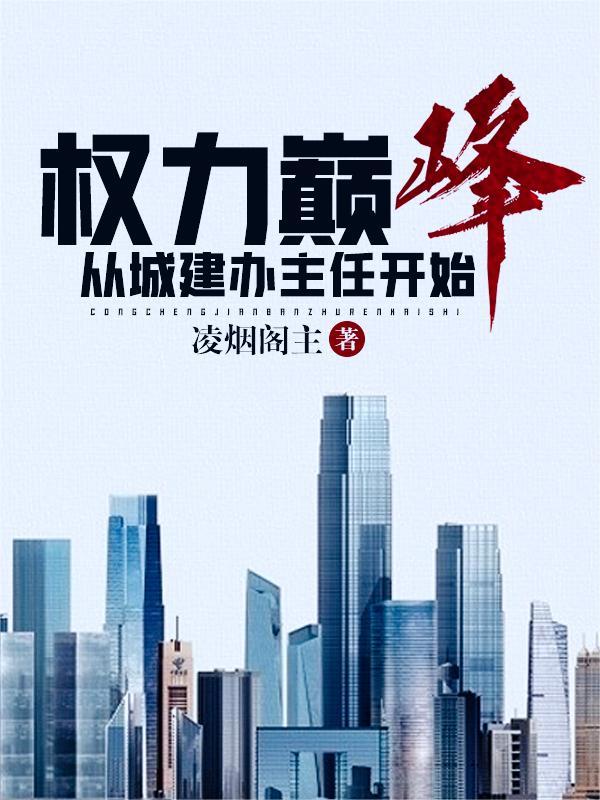旺仔小说网>清代后妃的品阶 > 第18章(第1页)
第18章(第1页)
⑤谨按,清代笔帖式亦有无品者。
是在世宗雍正帝创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前;第二种则是在创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后。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真正“分藩”。
有清一代,在雍正朝设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前,除皇太子外的成年皇子,均要出宫分府居住,制度上称为“就藩”“之藩”。皇子们封爵就藩之后,其旗籍从上三旗变为下五旗,同时获得自己新隶旗的数个佐领(牛录)旗分,以此成为此旗的领主之一。若其旗佐领(牛录)不足,还可以从上三旗分拨旗分佐领或者包衣佐领至五旗。以此为背景,皇子就藩分得旗分之后,属下拥有两方面的人员:一是自己府邸的包衣佐领、包衣管领下人,一般称为“府属包衣”;二是自己府邸的旗分佐领下人,一般称为“属人”。清初时,不仅府属包衣对自己的属主有繁杂的义务,属人对自己的属主也有相当的义务,其中即包括让子女侍奉属主。①因此,皇子府邸内的一些侍妾乃至于侧福晋,均为其府属人或府属包衣出身。一旦皇子继承大统、入主宫廷,其府邸内之妻妾即随其进入宫廷,成为后宫主位。如世宗雍正帝在继承大统之前,原恩封为多罗贝勒,后晋封为和硕雍亲王,分封在镶白旗,获得满洲佐领六个、蒙古佐领三个、汉军佐领三个作为属人,还获得若干个包衣佐领、管领作为府属包衣。其属人之中即有当时隶属镶白旗汉军的年羹尧一家。②
而在雍正朝设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后,凡有可能继承皇位之皇子即使予以封爵,却不再分府令其就藩,亦不分与旗分。故而,所以雍正朝之后皇帝的“潜瓜”,实际仍在宫内。因为其并未获得属人,在其潜邸侍奉者均为内务府籍的上三旗包衣人。如宣宗的和妃辉发纳喇氏,侍宣宗潜邸,称格格,在嘉庆十三年为宣宗生下第一子奕纬,由仁宗特赐为侧福晋;宣宗道光帝即位之后,其成为后宫主位,获封为和嫔,晋封为和妃。和妃之家族即出身内务府正白旗佐领下人,③属于典型的内务府包衣。
整体而言,在皇帝潜邸之中,一方面,其嫡妻均由宫廷指婚,大多为参加挑选八旗秀女的外八旗女子,与自身“属人”“府属包衣”无关。另一方面,在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①关于入关之后皇子封藩的情况,可参考杜家骥:《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》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8年,第264—305页。
②关于世宗雍正帝即位前的封旗情况,可参考杜家骥;《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1990年第4期。
③《奏为应挑女子内有和嫔亲兄之女另为一班事》内称,和妃家族属于内务府“正白旗贻恭佐领下”,道光二年二月二十日,档案号:05-0620-048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设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后,侍奉宫内潜邸者均是参加挑选内务府秀女的内务府包衣三旗女子,亦即被选中伺候皇子的官女子。所以,真正并非通过挑选八旗秀女或挑选内务府秀女而进入潜邸的,主要是尚未设立秘密立储制度时的世宗雍正帝潜邸时的一些侧室、妾室。
第四节蒙古王公之女入宫
蒙古王公之女,即蒙古盟旗贵族之女。作为背景,首先要区分蒙古盟旗与蒙古八旗。
清代广义上的“蒙古人”大致可分为两类:一类是居住在内外蒙古以及西北各地的蒙古人,他们被編入以部名取名的“旗”,各“旗”则隶属某个“盟”,如哲里木盟内,有科尔沁左翼后旗等旗。故此类被称为“蒙古盟旗”。另一类是清代入关之前或入关之初被編入八旗的蒙古人,他们大部分被编入蒙古八旗,小部分被編入满洲八旗,分属八种旗色,如镶黄旗蒙古人、镶白旗蒙古人等。故此类被称为“八旗蒙古”或“蒙古八旗”。这两类广义上的“蒙古人”有许多差异。对于宫廷而言,最大的差异在于,“蒙古八旗”出身的女性作为八旗旗人,必须参加挑选八旗秀女,而“蒙古盟旗”出身的女性则不在挑选范畴之内。与此相对,狭义上的“蒙古人”,经常专指蒙古盟旗之人。现在学术上所谓的“满蒙联姻”,其“蒙”所指亦是蒙古盟旗。
清代宫廷与蒙古盟旗的联姻从入关前即已存在,太祖弩尔哈齐曾娶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之女为侧福晋,即寿康太妃。太宗皇太极的“崇德五宫”亦均为蒙古盟旗出身。入关之初,这种与蒙古盟旗联姻之习惯也被清廷所继承,世祖顺治帝的废后(静妃)、孝惠章皇后均为科尔沁蒙古出身,其后宫主位内还有淑惠妃、恭靖妃、端顺妃、悼妃等数位蒙古盟旗出身的女子。但是,这种与蒙古盟旗联姻的习惯从康熙朝开始逐渐减少,圣祖康熙帝只有慧妃和宣妃等几位蒙古旗盟出身的后宫主位,高宗乾隆帝亦只有慎嫔等几位蒙古盟旗出身的后宫主位。这些成为后宫主位的蒙古盟旗贵族之女,均非通过制度上的挑选秀女而进入宫中。而从嘉庆朝开始直到清末,后宫主位中不再有出身蒙古盟旗之人,这种特殊的入宫方式也就不复存在。
第五节民籍汉人之女入宫
如前文所述,清世祖顺治帝在顺治五年(1648年)曾短暂地允许满汉结亲,但是不久之后,政策便发生变化,转而采取民间俗称为“满汉不通婚”的“旗民不交婚”的联姻禁止政策,直到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才由孝钦显皇后下令破除。与此同时,从清初到清末,民间一直有“宫中娶汉女”的说法。虽然清代官方对此数度驳斥,但是经过对宫廷档案的梳理,可以明确地得知清宫役使民籍汉女,甚至以之为后宫主位的事实。
顺治十二年七月,时任兵科右给事中的季开生上奏称:“近日臣之家人自通州来,遇见吏部郎中张九微回籍,其船几被使者封去。据称奉旨往扬州买女子。夫发银买女,较之采选淑女,自是不同。但恐奉使者不能仰体宸衷,借端强买,小民无知,未免惊慌,必将有嫁娶非时,骨肉拆离之惨……(中略)从来歌舞之席易生怠荒,历史垂戒,何庸臣赘。今当四方多警,楚闽用兵,正皇上励精图治,寝食不安之际,何不移此使以阅旅,省此费以犒军,鼓忠勇而励防剿之为愈乎。”对此说法,世祖覆谕:“前内官监具奏,乾清宫告成在即,需用陈设器皿等项,合往南省买办,故令发库银遣人往买。初无买女子之事。太祖太宗制度,宫中从无汉女。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训,岂敢妄行。即天下太平之后尚且不为,何况今日。朕虽不德,每思效法贤圣之主,朝夕焦劳。屡次下诏求言,上书禁勿称圣,惟恐所行有失。若买女子入宫,成何如主耶。”最终以“季开生身为言官,果忠心为主,当言国家正务实事。何得以家人所闻,茫无的据之事,不行确访,辄妄捏渎奏。肆诬沽直,甚属可恶”而“著革职,从重议罪具奏”。①这是清廷第一次对民间“宫中汉女”说法进行回应,也提出了“宫中从无汉女”的说法。而根据顺治十三年十月时抵达京师的朝鲜麟坪大君所著《燕途纪行》中记载“翰林石绅女,季秋选入,宠冠后宫”②,恪妃可能是在顺治十三年秋季入宫,恰恰与前一年世祖上谕中所提及的情况相抵触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①《世祖章皇帝实录》卷92,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条,《清实录》,第3册,第725页。
②[朝鲜]麟坪大君李澹:《燕途纪行》,林基中编:《燕行录全集》,首尔:东国大学校出版部,第22册,第134—139页。
在康熙朝,京旗贵族委托南方织造等官员在南方购买甚至拐骗民籍汉女,几乎成为当时的一种“流行”。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十七日,清圣祖康熙帝谕令工部尚书王鸿绪道:“前岁南巡,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,朕到家里方知。今岁又恐有如此行者,尔细细打听,凡有这等事,蜜蜜①写来奏闻。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,有人知道,尔即不便矣。”之后王鸿绪覆奏说:“今据所闻,先缮折密奏。访得:苏州关差章京买昆山盛姓之女,又买太仓吴姓之女,又买广行邹姓之女。……原任东平州知州范溥今捐马候补金事道,本籍徽州人……在常熟县以银五百两强买赵朗玉家人之子……又,范溥强买平人子女,皆托御前人员名色……侍卫五哥买女人一名,用价四百五十两。又买一女子价一百四十两,又一婢价七十两,方姓媒婆成交……此外,纷纷买人者甚多。或自买,或买来交结要紧人员,皆是捏造姓名虚骗成局。”②由“纷纷买人者甚多”一句,足可见此举在当时之盛行。
朝廷官员如此,宫中似乎也未必能够“免俗”。在清圣祖康熙帝的后宫主位之中,有不少均为汉姓,其中固然有安嫔这种出身汉军八旗,或端嫔这种出身内务府包衣汉姓人的情况,却也有相当一部分无法查到旗籍,很可能即出身民籍汉女。同时,一些档案也纷纷证明这一点。例如,康熙四十八年(1709年)七月十六日,时任管理苏州织造的李煦递交一份奏折,其中说道:“王嫔娘娘之母黄氏,七月初二日忽患痢疾,医治不痊,于七月十四日午时病故,年七十岁。理合奏闻。”清圣祖康熙帝的朱批则写:“知道了。家书留下了,随便再叫知道罢。”③这里的“王嫔娘娘”即是顺懿密妃。《玉牒》等书记载其为“知县王国正之女”。此折由苏州织造呈递,可以有两种解释:一是王国正是汉军旗人或内务府包衣汉姓人,在南方任知县,妻子随任,在南方病故;二是王国正并非旗人,而是苏州民籍汉人,顺懿密妃以民籍汉女入宫成为后宫主位。又如,在乾隆年间礼部和内务府、宗人府的行文中,曾经明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①即“秘密”。
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,北京:档案出版社,1984年,第1册,第613—615页。
③《奏为王嫔娘娘之母黄氏病故日期事》,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十六日,档案号:04-01-30-0006-004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确提及,“襄嫔父,原正定府民高廷秀……静嫔父,原陕西宁夏民石怀玉”。①道出了圣祖的襄嫔和静嫔均为民籍汉人之女之事实。
至于乾隆朝,早在高宗乾隆帝即位之初的乾隆三年(1738年)五月,即下达过这样的上谕:“朕自幼读书,深知清心寡欲之义……近闻南方织造、盐政等官内,有指称内廷须用优童秀女,广行购觅者,并闻有勒取强买等事,深可骇异。诸臣受朕深恩,不能承宣德意,使令名传播于外,而乃以朕所必不肯为之事使外间以为出自朕意,讹言繁兴。诸臣之所以报朕者,顾当如是乎。况内廷承值之人,尽足以供使令。且服满之后,诸处并未送一人。”②但在事实上,乾隆朝宫廷买人民籍汉女,甚至以之为后宫主位的档案,却相当丰富。
乾隆十三年(1748年)十二月,苏州织造图拉在正折之外附了一个折子,上报了这样的事情:
恭为附折奏闻事。奴才访得苏州潘姓女子,于前二年即密讫其亲族借称京官聘娶。其父虽允,其母决志不从,难以办理,后只得记原办之人缓图。今冬,因此女年已二十,家道寒苦,高低不就,其父允瞒妻女,奴才借称本地人,详细密看此女,举止甚庄重,身段、面貌俱韵雅。奴才即严嘱原办之人,瞒其父母,指京官聘娶。其父愿瞒妻女,于十一月二十夜静密接进署。奴才母亲、奴才女人俱敬为看过,缘此女不知道进京情由,甚游移不定,是以未敢具奏。奴才母亲细将进宫好处开导数日始觉释然相信。奴才拟于新年二月初旬由水路起程,约三月初旬可以到京。再,现在严令原办家人仍密遍访,或能再得一人,相随同进。为此恭将办理缘由并女子进署日期附折谨密奏闻。乾隆十三年十二月。奴才图拉。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