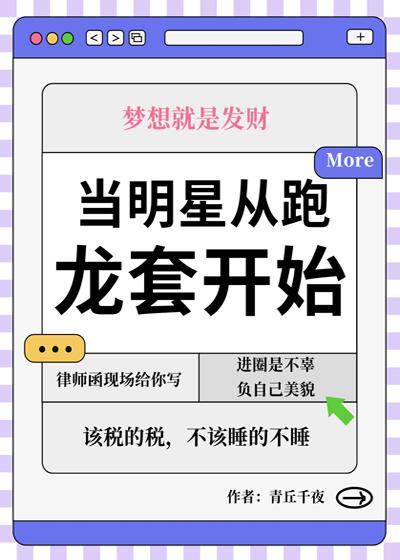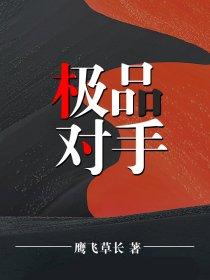旺仔小说网>嫁给病弱太女a后免费 > 第6章(第2页)
第6章(第2页)
元祯坚持,她又不是没见过苟柔在车上痛得龇牙咧嘴涕泪直流,“你就是块青铜,也不能糟践自个。”见苟柔气鼓鼓,她柔下声音:“孤身边有上官校尉呢,路上有他们照顾,阿柔只管放心。”
苟柔大声道:“哪个是担心你,奴婢分明一点事也没有。”
疼痛逼出的泪水差点盈满眼眶,她急于向元祯证明自己,转过身后才抹干泪花,僵着腿就去查点行装。
元祯紧蹙着眉头,喊了她几声,全都被无视,反倒听萧智容感慨道:“殿**恤下属,苟女史又忠心耿耿,真乃君臣的典范。”
“阿柔是先母拨到我身边的,只比我大几岁,却难得能事事照料妥帖,我对她的依仗也比旁人更多些。”
两人共度过先王后殒命、元祯瘫痪等许多难捱的时光,情意超过一般主仆,元祯早就将她视为亲姊。
“她不拘小节,路上难免会出个三长两短。”元祯忧心忡忡,她让人给自己披上件外袍,伸手推起四轮车轮子,向外追赶,“此去长安,本就凶险至极,我非要劝她留下来不可。”
万一那萧八娘翻脸不认人,既留下了郑虎符,又趁机扣他们在长安,阿柔岂不是要跟着遭殃?
“阿柔,阿柔。”
野外的庄子不比广陵城,只有在门口才挂有一盏纸灯笼,元祯在夜里视力偏弱,偏生又不认路,到处找不到苟柔,指挥着死士蒙头乱转。
喊了两声,即便无风吹来,元祯的身子骨让夜寒浸透,又是一阵咳嗽。
“殿下,是您吗?”
几盏方灯从拐角处缓缓步出,元祯抬头,昏黄的灯烛下是桓三娘柔美的脸庞,她见到元祯,微微有些惊讶,旋即又绽放出清浅的笑,“果然是殿下,妾方才还与婢子说呢,这声音听着像是殿下的。”
她眼中笑意温柔,元祯望向其身后,跟来的只有三名婢子,俱是坤泽,便稍稍放心,问:“三娘如何在此处?”
桓三娘微笑道:“今日宴罢,奴家与阿兄本要回邙山家中,不过王后使人说隔日还要开宴,如此一来,邙山便不能回了,恰好城外有桓氏的庄子,于是妾就来到此处暂住。”
夜里本就要安置了,又听外头人声沸腾,庄里的主子只有桓三娘与桓大郎,大郎胆子小,缩在被中不敢出头,桓三娘无奈,只得亲自带人出来查探。
哪知在这荒郊野岭,竟让她遇到太女殿下了呢。
因白日间的接触,桓三娘对文弱的太女产生了些许好感,夜里出人意料的重逢,让她的声音里都带有欣喜。
元祯见她事事亲为,便知庄中无长辈在,于是劝道:“你与大郎在外不安全,宫中不会再开宴了,明日启程早早回家吧。”
桓三娘轻轻“啊”了一声,她的眼眸真挚,语气里带着道不明的感情,“那么,殿下已经定好正妃人选了吗?”
若是太女妃已定,那确实是没有再开采选宴的必要了。
她不提还好,一提元祯也有些灰心丧气,整个人如落花一般萎下去,哪会这般快呢,宴席上娘子郎君嫌恶的神情,她到现在还记着呢。
“倒也不是这个缘故,是孤有事。”
元祯想到生死未卜的阿父与丹阳,脸上的笑渐渐消失,声音在如墨的夜里格外沉重。
桓三娘心地温柔善良,不明白她的苦衷,只以为太女还在为宴上的众人而烦恼,安慰道:“有缘千里会相见,殿下勿要忧心,一定会遇到意中人的。”
此话一出口,桓三娘发觉不妥,她不也正是备选太子妃的人之一吗,说这种话未免有将太女推出去的嫌疑。
虽然太女患有重疾,但其实……自己并没有这个意思。
夜幕低垂,仅有星光点缀。少女萌芽的心事、微红的脸颊、眼眸中期许的微光,在漆黑的夜晚荡漾流转。
元祯通通不知晓,她心思迟钝,目光仍在搜寻苟柔,忽然又问桓三娘:“三娘出来可带着医工?孤的女史摔伤了腿,又着急赶路,想求一方良药。”
桓三娘一怔,莫名的失落涌上心头,她想了想,道:“医工不曾带,不过妾的姑姑,曾是从前皇宫中的医工长,据说有救死扶生的本领,后来辞官在长安办斋堂,做了好些伤药寄给阿父,阿父用着说有奇效。奴家身边带了几贴,这就让人取来。”
元祯谢过她,又想桓三娘言行稳重,她道桓娘子的医术了得,想必是不会差,此去长安,何不也请桓娘子为自己的腿瞧瞧?
在四轮椅上磋磨久了,只要有一分能站起来的希望,元祯都不会放弃。
不过她要去长安的事,却不能对桓三娘说。
正踌躇如何开口询问,元祯冷不丁地听到桓三娘充满诚恳的话:“奴家的姑姑,讳灵媛,小时妾也在长安住过一段时日,曾亲眼见她治好一名腿脚有疾二十年的老翁,后来那老翁不论是骑马还是奔走,都不碍事。”
这时奴婢气喘吁吁的将伤药带来了,桓三娘接过,妥帖地递到元祯手中,触到太女肌肤冰冷,她既心疼又是鼓励道:“殿下年岁尚轻,何不请人去长安寻她一试?阿姑极好财,只要有重金相许,就算有几千里地的奔波,她都不嫌辛劳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