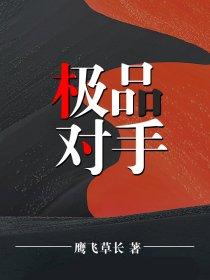旺仔小说网>食骨记火锅德化坪埔 > 金箔泣蟹饼救赎渡魂归(第1页)
金箔泣蟹饼救赎渡魂归(第1页)
一、夜市初遇:暖光里的蟹饼香
隋大业七年的扬州,腊月寒风裹着运河水汽,像细密的凉针拂过街巷,街旁红灯笼在风里晃出暖黄光晕,落在青石板上,成了寒夜中难得的温柔亮色。陈墨裹紧身上洗得发白的棉布短衫,布料薄得能看见内里三层补丁,袖口短了半截,露在外面的手腕冻得泛红。这是他三天前来到这里后,在街角旧衣铺用父亲留下的银钗换来的——那银钗是父亲陈砚山早年走遍江南寻来的老物件,钗头刻着小巧莲花,曾陪着陈墨拍下无数美食照片,如今却只能换一件勉强蔽体的旧衣。
他下意识攥紧怀里的银汤勺,勺身缠著浅浮雕缠枝莲纹,在灯笼光下泛着淡银光泽。指尖触到冰凉金属的瞬间,心头竟生出几分安定,仿佛父亲的气息还萦绕在侧,陪他应对这全然陌生的时代。从清晨到日暮,陈墨在扬州街巷里转了大半日,眼里是宽袖襦裙的行人、飞檐翘角的宅院,耳边是软糯却难懂的吴侬软语,胃里的空荡让记忆里父亲做的腊骨汤香气愈发清晰——那汤要慢炖三个时辰,腊骨咸香渗进汤底,再丢一把干笋,喝一口便能从喉咙暖到心口。
就在陈墨靠著斑驳砖墙叹气,琢磨着今晚去哪寻口热食时,一股鲜醇香气忽然钻进鼻腔。不是腊肉的厚重,也不是米面的清甜,是蟹肉独有的鲜,混着炭火烤出的焦香,还裹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,像极了父亲曾在苏州平江路拍过的蟹粉小笼,却多了几分烟火气的质朴,勾得他腹中饥饿瞬间翻涌。
陈墨循着香气拐进窄巷,刚踏入便被夜市喧闹拥住:挑担小贩吆喝着“热汤面嘞——刚煮好的热汤面”,声线洪亮;绿裙姑娘们手挽手,捏着油纸包笑谈胭脂好坏;半大孩子追着花猫跑,笑声清脆。而巷尾炭炉旁,裹着灰布头巾的老妪正弯腰,用小铁铲轻轻翻烤圆饼。
饼子比铜钱略大,表面撒着白芝麻,在炭火上烤得金黄,油星子“滋滋”溅在炭上,腾起的白烟裹着香气飘散开,引得路过孩童驻足,仰着脖子眼巴巴望着,手里攥着铜钱却舍不得立刻花。陈墨走上前,喉咙发紧——这是他来到这里后第一次与人搭话,既紧张又怕口音露了异常。他清了清嗓子,尽量让语气平和:“阿婆,这饼怎么卖?”
老妪抬头,脸上皱纹挤成深深沟壑,眼神却透着温和。她上下打量陈墨片刻,笑着说:“客官是外乡人吧?听口音不像咱们扬州的。这是金钱蟹饼,一文钱一个,刚出炉还热乎,你尝尝?”说着,她用粗糙如老树皮的手捏起一个蟹饼,用油纸包好递来。陈墨接过,油纸裹着的温度透过指尖传来,竟让他眼眶微涩——这温度,和小时候父亲冬日归来时递给他的烤红薯一模一样,都是寒夜里最踏实的暖意。
陈墨赶紧摸出怀里仅剩的几枚铜钱,刚要递过去,老妪却摆了摆手把他的手推回:“看你面生,许是刚到扬州迷了路?这饼送你尝,相逢即是缘,不用给钱。”陈墨愣住,没料到在陌生地界能遇这般善意,攥着蟹饼的手都暖了几分。他刚想道谢,指尖的银汤勺忽然轻轻发烫,他没在意,只当是炭炉热气熏的,低头咬了一口蟹饼。
“咔嚓”一声,饼皮脆得刚好,蟹肉颗粒在口腔里散开,鲜甜瞬间漫开,面粉的绵软裹着蟹鲜,还带着一丝极淡的金属甜意,不似糖般腻人,反倒清爽解了蟹的腥气。可就在这时,陈墨忽然觉出一缕异样的凉——不是味觉的凉,更像一种藏在饼里的委屈情绪,像少女低低的啜泣,还裹着几分焦急。
“嗯?”陈墨皱眉,刚想细品,怀里的银汤勺突然猛地发烫,烫得他下意识松手,汤勺“当啷”掉在青石板上。他赶紧弯腰去捡,低头时却见勺身映出的不是自己——是个穿粗布裙的少女,梳着双丫髻,发梢沾着点面粉,手里攥着块没烤的蟹饼,眼睛红红的满是焦急,对着他轻轻叹息,嘴唇动着像想说什么,却发不出声音。
“这……”陈墨惊得后退一步,手里的蟹饼差点掉了,汤勺在地上滚了一圈撞在墙根,少女的影子瞬间消失,勺身又恢复原本模样,只映着青石板纹路。老妪看见那银汤勺,眼神忽然暗了,她放下铁铲慢慢蹲下身,用袖口擦了擦勺身灰尘,递还给陈墨时声音带着微颤“客官这勺子,是能看见些特别的东西吧?”
陈墨攥紧汤勺,指尖烫意还没散,看着老妪眼里的哀伤,他点了点头,声音发紧“刚……刚才看见个姑娘,穿粗布裙梳双丫髻,像在叹气流泪。”老妪的眼泪突然掉下来,一滴一滴落在炭炉旁的青砖上,晕开小片湿痕。她用袖子擦了擦眼睛,哽咽着说“那是我女儿阿桃。三年前闹饥荒,地里颗粒无收,家里连米都没了,她弟弟饿得直哭。阿桃心疼弟弟,偷偷把我早年给她备的嫁妆金镯拿出去,找银匠熔成金箔碎裹在蟹饼里,想进城换点粮食回来……”
老妪的声音越来越轻,像要被风吹散,陈墨的心也跟着沉下去。他想起父亲曾说,过去饥荒年月,一块干饼就能救命,那时他只当是故事,此刻从老妪的眼泪里,才懂了食物背后的重量——那不是简单的果腹,是绝境里的希望,是亲人之间的牵挂。
“那天早上,阿桃揣着二十个蟹饼出门,跟我说‘娘,等我回来,就能给弟弟煮米粥了’。我在门口等了她一夜,从日出等到日落,又等到天亮,没等来粮食,只等来隔壁张婶说,她在城门口看见阿桃被两个官差拦住。那些人抢了阿桃的蟹饼,看见里面的金箔就起了争执,后来阿桃就没再回来……”老妪抹了把泪,指了指面前的炭炉,“之后我就接着烤蟹饼,总觉得她还在我身边,说不定哪天就提着粮食回来喊我‘娘’。每次烤饼,饼芯里都能看见金箔闪,有客人咬到金箔,还会听见阿桃喊‘弟弟’,我知道,她是放心不下弟弟,想看着弟弟好好的。”
陈墨握着银汤勺的手紧了紧,指节泛白,勺身又开始发烫,这次映出的画面更清晰:阿桃穿着粗布裙,怀里紧紧抱着布包,缩在城墙根想悄悄进城,却被两个官差拦住。官差抢过她的布包,掏出蟹饼看见金箔,眼神亮了起来。阿桃急着去抢,喊着“那是给弟弟换粮食的”,可她一个姑娘家哪里争得过?后来官差推了她一把,阿桃没站稳撞到旁边的摊子,之后便没了动静,她的蟹饼被官差揣进怀里带走了……
“阿桃的弟弟呢?”陈墨声音发紧,想起小时候父亲总把最好的留给自己——有次他发烧,父亲连夜跑三条街买他爱吃的草莓,那种亲人的牵挂,哪怕没经历过姐弟情,也能从阿桃的执念里清晰感受到。
老妪听到“弟弟”两个字,眼泪掉得更凶“饥荒最厉害的时候,我带着阿桃的弟弟阿树来找她,可城里到处是逃荒的人,找了半个月也没消息,干粮也吃完了。有天晚上在破庙睡觉,早上醒来阿树就不见了,我喊着他的名字找遍破庙也没找到。这三年,我一边烤蟹饼一边找,可扬州城这么大,我一个老太婆,哪里找得到?”她的声音满是绝望“阿桃的魂缠在饼里,就是想让我找到阿树,让阿树知道,姐姐从来没忘了他,还想着给他换粮食呢。”
陈墨低头看着手里的蟹饼,金箔的甜意还在舌尖,却多了几分苦涩。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“这勺子能尝出食物里的心意”,以前只当是玩笑,此刻才懂——这“心意”里,既有温暖的善意,也有没完成的牵挂,是藏在食物里、跨了生死的执念。
“阿婆,我帮你找阿树。”陈墨握紧银汤勺,勺身温度渐渐稳了,隐隐透着指引的方向“阿桃的魂在汤勺里,她肯定知道阿树在哪,会带我找到他的。”
老妪抬头,眼里满是不敢置信,随即燃起一丝希望“真……真的能找到阿树吗?”
陈墨用力点头“我试试,一定尽力。”
接下来三天,陈墨每天天不亮就出门,跟着银汤勺的指引在扬州街巷里转。银汤勺像有生命,靠近可能有阿树踪迹的地方就会轻轻发烫,还会映出淡影。第一天,汤勺指向东市破庙,陈墨在那里找到一群流浪孩童,最小的五六岁,最大的也才十岁,他们蜷缩在破棉絮里,看见蟹饼眼睛都亮了。陈墨把蟹饼分给他们,问有没有见过叫阿树的男孩——七八岁,怀里抱个布偶,孩子们却都摇头说没见过。
第二天,汤勺指向西巷粥棚。那是城里富户捐钱搭的,每天中午给逃荒的人施粥。陈墨排在长队里攥着汤勺,轮到他时汤勺突然烫了,他四处张望,看见粥棚旁台阶上坐着个白发老人,怀里抱着个孩子,可那孩子才三四岁,不是阿树。老人说那是他孙子,家里人都没在饥荒里,也没见过叫阿树的孩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