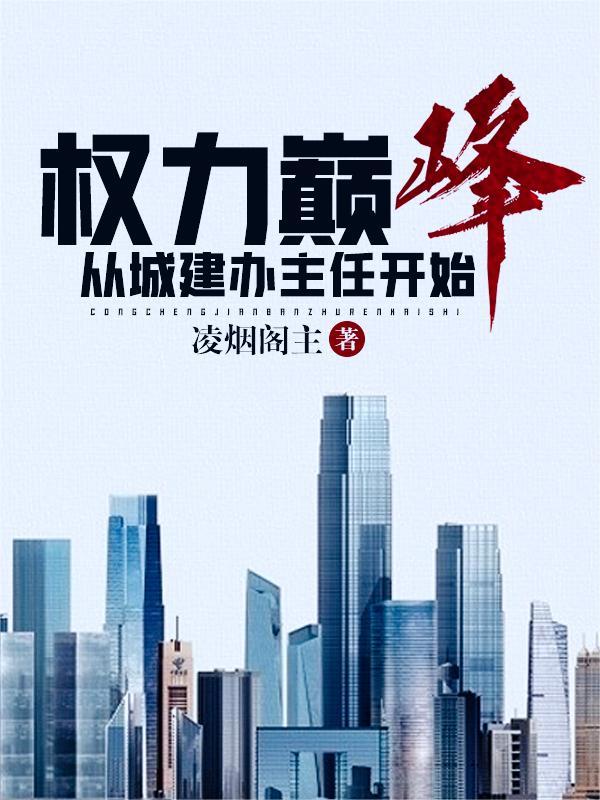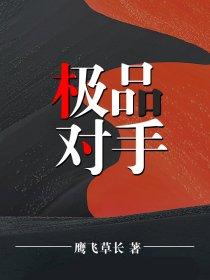旺仔小说网>飞龙传 > 第 23 章(第1页)
第 23 章(第1页)
话说后汉年间,邺都帅府的内堂里,烛火通明,郭威正陪着姑丈柴守礼、姑母柴氏一家三口围坐饮酒。桌上摆着酱肘子、烧羊肉,还有一壶刚温好的汾酒,酒香混着肉香,满屋子都是暖意。郭威今年已近五十,两鬓添了些白发,可眼神里满是雄心——这些年他跟着刘知远打天下,如今手握兵权,心里早有了称帝的念头,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说出口。
酒过三巡,郭威端着酒杯叹了口气:“姑丈,不瞒您说,我这心里头啊,总想着干一番大事业。如今朝廷动荡,百姓受苦,我要是能执掌大权,定能让天下太平。”这话正说到柴荣心坎里——柴荣是柴守礼的儿子,从小就跟着郭威,早就把这位姑爹当成了靠山。他心里暗忖:“姑爹年纪大了,又没儿子,将来这位置迟早是我的。不如趁今天探探他的口风,要是能定下个名分,往后就好办了。”
柴荣放下酒杯,脸上堆着笑:“姑爹,您常说自己身上有奇相,能成大事。小侄斗胆,想亲眼瞧瞧,不知姑爹肯不肯?”郭威这会儿已有三分酒意,听柴荣这么说,顿时捋着胡子哈哈大笑:“贤侄想看有何不可?要是我这‘雀儿’真能跟‘谷稔’凑到一块儿,将来我当了皇帝,就封你当守阙太子,接我的班!”
柴荣一听,心里乐开了花,赶紧离席磕头:“谢姑爹恩典!”郭威更高兴了,叫过旁边伺候的丫鬟春桃和秋菊:“你们俩过来,帮我把外袍和中衣脱了,让柴贤侄瞧瞧。”两个丫鬟手脚麻利地帮郭威宽了衣,露出两条胳膊——左胳膊上长着个拳头大的肉瘤,形状像只展翅的雀儿;右胳膊上则有个谷穗似的疙瘩,两者之间隔着五寸多远,看着就像两尊小山峰。
柴荣凑上前,心里怦怦直跳——他既盼着这两物能靠在一起,又怕姑爹看出自己的心思,手都有点发颤。他一只手轻轻按住“雀儿”,另一只手按住“谷稔”,慢慢往中间挤。没想到这一挤,那“雀儿”竟真的往“谷稔”那边挪了挪,最后竟完完全全贴在了一起!柴荣又惊又喜,高声喊道:“姑爹!雀儿进到谷稔里了!”
郭威一开始还以为是柴荣故意挤的,笑着说:“贤侄,你用手按着,当然能凑一块儿,松开手还能粘住不成?”柴荣赶紧松开手,可那“雀儿”竟像长在了“谷稔”上似的,纹丝不动!柴荣傻了眼,心里嘀咕:“刚才还隔着五寸远,怎么这会儿真粘住了?难道真是天意?”他赶紧喊柴氏:“姑母,您快来看!这雀儿真跟谷稔连在一起了,不是我骗人!”
柴氏走过来一看,果然不假——两条胳膊上的异相紧紧粘在一块儿,分毫不差。她赶紧对郭威说:“老爷,你快看看!侄儿没说瞎话,要不咱把穿衣镜抬来,你自己瞧瞧!”郭威也慌了,叫春桃和秋菊把堂屋里那面一人高的穿衣镜抬过来,又拿了面菱花小手镜,对着穿衣镜前后照。这一看,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两物相连,心里顿时乐疯了,手舞足蹈地喊:“妙啊!妙啊!这是天意要我成事!贤侄,多亏了你,往后我必不负你!”
说着,郭威叫人重新摆酒,又加了两道菜——一道清蒸鲈鱼,一道炒虾仁,四个人边喝边聊,直到半夜才散。柴荣回房后,翻来覆去睡不着,心里满是憧憬:“姑爹封我当太子,将来我就是皇帝了!得好好干,不能让姑爹失望。”而郭威则对着镜子里的异相,暗下决心:“时机差不多了,该找机会把大权攥在手里了。”
第二天一早,郭威升帅府大堂,手下将领都来参拜。他当着众人的面,封柴荣为帐下参军,负责运筹帷幄。接着,他故意皱着眉说:“如今我奉王命守这邺都,可兵力太少,怕挡不住敌军。柴参军,你去四门立起旗号,招兵买马,挑选能征善战的勇士。这事关国家安危,你可不能马虎!”
其实郭威是故意这么说——他明着是让柴荣招兵,暗地里是让柴荣培养自己的势力,为将来称帝铺路。柴荣心里明白,赶紧领命:“谢姑爹信任!小侄定不辱使命!”他挂了参军印,出了帅府,立刻让人在东西南北四门立起“招兵”大旗,又贴了告示:凡年满十六、不满五十,身强力壮者,均可参军,待遇从优。
消息一传开,四方的好汉都来了——有庄稼汉,有猎户,还有退伍的老兵,没几天就招了三千多人。柴荣亲自挑选,把身手好的编到精锐营,还请了老将领教武艺。他心里盘算着:“这些人都是我的心腹,将来姑爹成事,全靠他们了。”
咱们暂且不说柴荣招兵买马的事,再说说赵匡胤。他在兴龙寺住了一个多月,每天跟着玄真长老练拳,日子过得倒也安稳。可赵匡胤是个闲不住的人,总想着出去闯荡,干一番大事业。这天一早,他就收拾好了行李,去见玄真长老。
玄真长老正在佛堂念经,见赵匡胤进来,就知道他要走。长老叹了口气,从怀里掏出个黄布包的平安符:“匡胤啊,你这一去西行,路上可不太平。初冬时节天寒,山路又滑,这平安符是老衲在佛前供了三个月的,你带着,能保你一路顺遂。记住,遇事多忍忍,别像上次在董家酒楼似的,动不动就跟人动手。”
赵匡胤接过平安符,心里暖烘烘的,眼眶有点红:“师父,您放心,我这次一定收敛性子。等将来我有了出息,就回来给寺庙添香油,再给您盖座新佛堂!”师徒俩又聊了会儿,玄真长老叫人备了酒菜,为赵匡胤饯行。
吃过饭,赵匡胤把盔甲、行李捆在马背上,神煞棒系在腰里,翻身上马。玄真长老带着众僧送到山岔路口,再三叮嘱:“路上多保重,遇到难处就找当地的寺庙,僧人们会帮你。”赵匡胤点点头,勒转马头,挥了挥手:“师父,弟子走了!”说完,一拍马屁股,朝着西边疾驰而去。
此时已是初冬,路边的草都黄了,风一吹,卷起地上的落叶,带着股凉意。赵匡胤骑着马,心里又激动又迷茫——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,也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,只想着能遇到识才的人,施展自己的本事。
跑了约莫两个时辰,赵匡胤有点渴了,正想找个地方喝水,忽然看见路边有座花园。那花园围着竹篱笆,里面没种别的树,就栽了几十棵桃树。奇怪的是,这时候都入冬了,桃树上竟挂着十几个碗口大的鲜桃,红扑扑的,还带着水珠,看着就好吃。
赵匡胤心里纳闷:“这冬天怎么还有鲜桃?难道是用了什么法子养的?还是这地方的气候特别?”他越看越馋,口水都快流出来了,不知不觉就跟着马进了花园。到了桃树下,他跳下马,把马拴在篱笆上,伸手摘了个桃子——果皮薄得能看见里面的果肉,咬一口,又香又甜,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流,比夏天的桃子还好吃。
原来这桃叫“雪桃”,三月开花结果,园丁们用暖棚捂着,精心照料到冬天才能成熟。要是下了雪,桃子上沾着雪,看着更娇艳,味道也更甜,是当地有名的特产,每年都要进贡给官府。后来金兵南下,打到陕西,把种雪桃的园子烧了,这雪桃就绝种了,实在可惜。
赵匡胤吃完一个,觉得不过瘾,又摘了一个吃。这时候他才想起,不能白吃人家的桃子——园丁们肯定花了不少心思,要是不给钱,心里过意不去。他摸了摸腰里的钱袋,掏出二十文钱,用草绳穿了,挂在桃树枝上,心里想:“一个桃子十文钱,两个正好二十文,不算亏了他们。”
刚挂好钱,赵匡胤又想:“这么好吃的桃子,不如再摘两个带着,路上饿了吃。”他又拿出二十文钱挂上,伸手去摘桃。可刚摘下来,就听见竹篱笆那边有动静——原来是看桃的丫鬟小翠。小翠今年十五岁,跟着主人李翠莲看园子,刚才她在屋里缝衣服,听见外面有动静,就偷偷来看,正好看见赵匡胤摘桃。
小翠吓得赶紧往屋里跑——她知道自家主人的脾气。李翠莲今年三十多岁,力气大得能举起百斤重的石头,性子比男人还烈,因为长得黑,脸上还有块疤,别人都叫她“母夜叉”。她嫁给猎户李忠后,就在家种雪桃,靠卖桃和进贡过日子,谁要是敢动她的桃子,她能跟人拼命。
小翠跑进屋里,喘着气说:“主、主人!不好了!园子里有人偷桃!”李翠莲正在磨两根生铁锤头——这是她防身的兵器,听见这话,把锤头往桌上一摔,骂道:“哪个不长眼的敢来偷我的桃!这可是要进贡给节度使的,少一个都要掉脑袋!”她提起锤头,迈开大步就往园子里跑,心里还琢磨:“要是真丢了桃,我非把这偷桃的大卸八块不可!”
赵匡胤刚把桃子揣进怀里,就听见身后有人喊:“哪里来的贼,敢偷老娘的桃!”他回头一看,只见一个黑壮的妇人,手里提着两根铁锤,满脸怒气地冲过来。那妇人头发梳成三绺,用红头绳扎着,穿一件玄色短衫,绿裙子下摆掖在腰里,露出一双缠过的小脚,可跑起来比男人还快。
赵匡胤赶紧陪笑道:“大嫂,别生气,我不是偷桃,是买桃吃。我已经把钱挂在树上了,你去看看就知道。”李翠莲哪里肯信,举起锤头就往赵匡胤头上砸:“你这红脸贼!还敢狡辩!这桃是进贡的,就算你给一百文钱,也不能吃!”
赵匡胤赶紧侧身躲开,锤头砸在地上,把土砸出个小坑。他心里有点火了:“我都说了给了钱,你怎么还动手?古话说‘不知者不罪’,我又不是故意的。”李翠莲更生气了,又是一锤砸过来:“你私吃贡物,就是死罪!还敢跟老娘讲道理!”说着,挥舞着锤头,没头没脑地打过来。
赵匡胤本来不想跟女人动手,可李翠莲越打越凶,他只好躲来躲去。后来实在忍无可忍,趁着李翠莲又一锤砸过来,他往旁边一闪,伸脚一绊——李翠莲重心不稳,“扑通”一声摔在地上,锤头也掉了。赵匡胤赶紧上前,一脚踩住她的胳膊,随手折了根桃枝,对着她的后背轻轻打了几下:“大嫂,你还敢打吗?再打我可不客气了!”
李翠莲疼得直咧嘴,可嘴上还硬:“你敢打老娘!我丈夫回来饶不了你!”赵匡胤听了,又用桃枝打了几下,李翠莲终于熬不住了,哭着喊:“好汉饶命!我不敢了!你要吃桃就吃,我不拦你了!”
赵匡胤这才松开脚,把桃枝扔了:“早这样不就好了?以后别这么凶,对人客气点。”李翠莲爬起来,披头散发的,脸上还有土,被两个丫鬟扶着,一瘸一拐地往屋里走。回到屋里,她越想越气,拍着桌子哭:“这红脸汉子太欺负人了!等我男人从山里回来,我一定要找他报仇!”
赵匡胤没管李翠莲,把怀里的桃子揣好,解开马缰绳,翻身上马,继续往西走。跑了大约二里地,看见路边有块界碑,上面写着“千家店”三个大字。他心里一喜:“正好,找个店住下来,歇歇脚。”
进了千家店,赵匡胤看见路边有个“王记酒店”,就跳下马,把马和行李交给店小二孙二,说:“把我的马牵去喂点料,再给我找间干净的屋子。”孙二是个机灵人,赶紧接过缰绳:“客官您放心,我这就去办!”
赵匡胤提着神煞棒,进了酒店。店里摆着四张桌子,有两个客人正在喝酒。他找了个靠窗的桌子坐下,孙二端来一壶茶:“客官,您想吃点什么?我们这儿有酱牛肉、炒鸡蛋,还有刚炖好的羊肉汤。”赵匡胤说:“来一盘酱牛肉,一碗羊肉汤,再要两个馒头。”
没过多久,菜就端上来了。赵匡胤正吃着,店主王老实走了过来。王老实五十多岁,头发都白了,脸上满是皱纹,一看就是个老实人。他拱了拱手:“客官,您从哪里来啊?”赵匡胤放下筷子:“我从东边来,要往西边去。老掌柜,您贵姓啊?”王老实笑着说:“我姓王,叫王老实,这店是我爹传下来的。您叫我老王就行。”
两人正聊着,孙二慌慌张张地跑进来,声音都发颤:“掌柜的!不好了!明日是十五,抹谷大王的人来说,要咱们交三十石谷,还得您亲自去抹谷,不能找人替!要是不从,就要烧店!”
王老实一听,脸都白了,搓着手,在屋里转圈:“这可怎么办啊?咱们哪有三十石谷啊?上次张大叔家没交,店都被烧了,一家老小都没地方去……”赵匡胤听着纳闷,问道:“老掌柜,这‘抹谷大王’是谁啊?什么叫‘抹谷’?怎么还要交谷?”
王老实叹了口气,坐下来,慢慢说道:“客官,您有所不知。这西边二十多里有座太行山,山上有伙强盗,为首的叫威山大王,还有个巡山太保,手下有五千多人,到处欺负百姓。上个月又来个抹谷大王,姓周,叫周通,坐第三把交椅。这周通好吃狗肉,每次煮了狗肉,就带着人到镇上,挨家挨户让百姓‘抹谷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