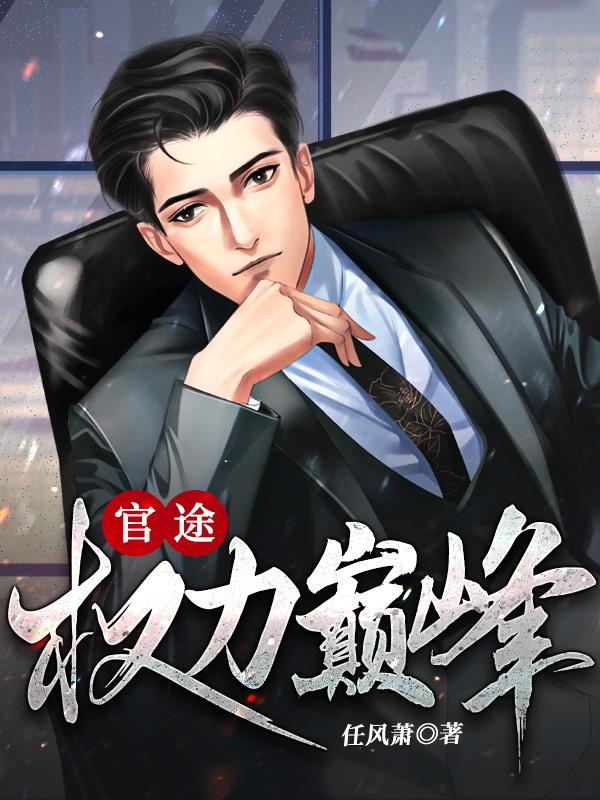旺仔小说网>飞龙传 > 第 44 章(第1页)
第 44 章(第1页)
话说周世宗柴荣见赵匡胤的罪是免了,可周天子只拨了三千兵马,要他去潼关捉拿高行周,用功劳抵消过错,心里头直打鼓,转头就找苗光义想办法。苗光义捋着下巴那撮山羊胡,慢悠悠道:“千岁您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。世上的事本就有兴有败,都是天数定好的,强扭不来——就算是再厉害的英雄好汉,也拗不过老天爷的安排。你看那诸葛亮,有经天纬地的本事,能想出鬼神都猜不透的计谋,一辈子为蜀国鞠躬尽瘁,最后还不是死在秋风吹拂的五丈原?还有项羽,能把大山似的鼎举起来,一声怒喝就能吓瘫上千人,可一旦时运没了,还不是在乌江边上抹了脖子?古往今来多少能征善战的将军,运气好的时候顺风顺水,运气差的时候连主意都拿不定。我昨晚夜里看天象,见高行周的命星暗得快掉下来了,瞧着活不了多久,早没多少能耐了。如今赵公子只要鼓足勇气往前去,见机行事,顶多两个月,高行周肯定得死,到时候公子您就能立下别人一辈子都赶不上的大功。”
苗光义这话刚说完,旁边的赵匡胤就“嗤”地冷笑一声,扯着嗓子喊:“苗光义,你这牛鼻子老道!仗着自己会说几句空话,把瞎话编得天花乱坠,就想糊弄人?我这次去要是能打赢回来,就算了;要是打不赢,不把你腿筋挑断,我就不姓赵!”苗光义听了也不生气,反倒笑得更欢:“赵公子,你这是聪明了一辈子,偏偏这时候犯糊涂。你要是真应了我的话,杀了高行周,得胜回朝,到时候别说打我,恐怕还得拎着好酒来谢我呢!可要是杀不了高行周,你自己都死在潼关了,哪还有命回来断我的腿筋?公子尽管放心去,保准能成。我就在王府里等你的好消息,到时候还得陪你喝庆功酒呢。再说了,换别人领兵去,未必能砍下高行周的脑袋,可你跟他是前世的冤家、今生的对头,这是定死了的事,犯不着瞎琢磨。”
赵匡胤被他噎得说不出话,心里却翻来覆去地打鼓:高行周那杆祖传的花枪,谁不知道厉害?连铁枪王彦章都死在他手里,我哪打得过他?可转念又想,做人这辈子,总不能贪生怕死,等着让人捆起来砍头吧?要是因为之前的罪过被杀,死得不明不白;倒不如战死在沙场上,还能留个好名声传后世。主意一打定,他冲着柴荣大声说:“大哥,快去挑选兵马!我明天就出发,就算高行周有三头六臂,我也跟他拼了,不死不休!”柴荣见他下了决心,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,立刻往教场去点了三千精锐,全交给了赵匡胤。
赵匡胤把兵马在城外扎好营,连夜赶回家里辞行。一进门就见父亲赵弘殷坐在太师椅上,脸拉得老长,一句话都不说,眼里满是火气;母亲杜夫人终究是疼儿子,一看见他,眼泪就掉了下来,拉着他的袖子问:“我儿,你可算回来了?”赵匡胤点头:“娘,我回来了。”
赵弘殷这时候再也忍不住,手指头戳着他的额头,声音都发颤:“你这不成器的东西!我跟你说过多少回,别在外头惹祸,好歹让我和你娘多活几年!你偏不听,一次次闯祸,害得我们老两口提心吊胆。如今你还回来做什么?赶紧走,别在我跟前碍眼!”赵匡胤知道父亲是嘴硬心软,赶紧跪下解释:“爹,娘,周天子虽然免了我的罪,却要我带罪领兵,尽快去潼关捉拿高行周回来立功赎罪,我明天就要走,特意回来跟你们辞行。”
杜夫人一听这话,当场就哭出了声,抱着赵匡胤的胳膊不肯放;赵弘殷虽说刚才还在发火,可听见周主要儿子去潼关打高行周,明天就出发,吓得魂都快飞了——那高行周是什么人物?儿子这一去,怕是凶多吉少。他别过脸擦了擦眼泪,声音哽咽着说:“匡胤我的儿,我白养你一场啊!你这去潼关,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,恐怕今天见这一面,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。”说着就不住地叹气,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。
赵匡胤赶紧扶着父亲的胳膊起身:“爹,高行周也是个人,又不是真有三头六臂,您别这么怕他。”赵弘殷狠狠瞪了他一眼:“你这畜生懂什么!那高行周精通兵法,还能看懂天象,排兵布阵跟孙武、姜子牙似的,一杆枪打遍天下没对手,连算卦都能断出吉凶,闻闻风向就知道输赢,捏把土就能猜出战局。你这是蚂蚱嫌路窄、雏鹰刚飞就嫌天低,根本不是他的对手,去了就是送死!我也没别的话说,就给你几句行军的规矩,你可得牢牢记住,照着做,或许还能留条命回来。你听好了:
沿路别伤着老百姓,天黑前一定要扎好营;
拔营得等太阳出来,选营地得找平坦安稳的地方;
夜里要防着敌人劫营,打更的得把时辰报清楚;
低洼的地方要防着人家放水淹营,窄道上得盯着别让人放火;
出兵得挑吉利的日子,打仗尽量占上风的位置;
追敌人的时候要防着埋伏,回营后得想着人家会不会反扑;
高行周的计谋多着呢,最会引诱你上当,挫你的锐气;
输赢虽然没法提前定,好歹听天由命,多靠脑子别蛮干。”
这几句都是赵弘殷打了一辈子仗总结的经验,他怕儿子记不住,特意念得慢,还拍着赵匡胤的手强调:“这都是保命的法子,你千万别仗着自己力气大就胡来,误了大事!”赵匡胤恭恭敬敬地应下,又对父母说:“爹,娘,我这去顶多半年,少则四个月,肯定能得胜回来,你们别担心。皇命在身,我不能多留,这就给你们磕头辞行。”说着磕了四个响头,转身要走。杜夫人哭着扯住他的衣角,怎么都不肯放,那场面跟生离死别似的,任谁看了都心酸。赵弘殷叹了口气,劝道:“夫人,孩子有大事要做,别拦着他了,让他走吧。”杜夫人这才依依不舍地松了手。
赵匡胤抹着眼泪出了正屋,往后院去辞妻子贺金蝉。贺金蝉早就听说丈夫要去潼关,心里头七上八下的,见他进来,赶紧迎到屋里,两人坐下后,她眼圈红红地说:“夫君,我听说朝廷免了你的罪,却又要你领兵远行,心里实在害怕。你这去可得求神明保佑,早点打赢回来,到时候我去拜天地、拜祖宗,好好谢恩。”赵匡胤握着她的手:“贤妻别担心,我进来是有件事托付你——爹娘年纪大了,早晚伺候的事,全靠你多费心。”贺金蝉点头:“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,你不用特意嘱咐。”说着,夫妻二人一起走到前厅,贺金蝉站在门口,看着他的背影,眼泪又掉了下来。
赵匡胤又回到正屋,跟弟弟赵匡义道别。他攥着赵匡义的手,声音低沉:“兄弟,我这去潼关,凶多吉少。要是我真死在高行周手里,爹娘年纪大了,就靠你尽孝;你嫂嫂还年轻,让她再找个人家,别让她守一辈子活寡。”赵匡义眼泪哗哗地流,攥着他的手不肯放:“哥哥你放心去,肯定能逢凶化吉,我在京城等着给你接风!”说着送他出了大门。
赵匡胤骑上马,往柴荣的王府去,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。柴荣早就备好了饯行的酒席,摆在书房里,就等他来。当时柴荣、赵匡胤、郑恩、张光远、罗彥威、赵普六个人按辈分坐下,只有苗光义不吃荤,特意给他摆了一桌素席。几人端着酒杯互相敬酒,夹着菜聊天,席间说的全是行军打仗的事。眼看着天快黑了,又喝了几杯,才撤了席,各自回房休息。
第二天一早,赵匡胤跟众人辞行,带着三千兵马,和郑恩一起,放了三声炮仗,浩浩荡荡地出了汴梁城,往潼关的方向走。走了没几天,路过昆明山,收服了山上的董龙、董虎兄弟——这俩人原本是占山为王的好汉,手下有八千喽啰,见赵匡胤是条英雄,又听说要去打高行周,当场就答应归顺,两路人马合在一起,一共一万一千人,队伍一下子壮大了不少。
又走了几天,路过张家莊,赵匡胤才知道张太公已经去世了。他赶紧让士兵备好祭品,亲自去张太公的灵前祭拜——当年他落魄的时候受过张太公的恩惠,如今张太公不在了,总得尽份女婿的礼数。张太公活着的时候家境殷实,可没儿没女,也没什么亲戚。赵匡胤叫来了张家的仆人和家童,挑了个忠厚老实的管家,让他负责照看张家的田地,逢年过节给张太公上坟;又嘱咐其他人要好好干活,不许偷懒耍滑,更不许欺负管家。众人都恭恭敬敬地应了。赵匡胤安排好这些事,才带着兵马继续往前走。有诗为证:
董家兄弟八千兵,归顺之后军纪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