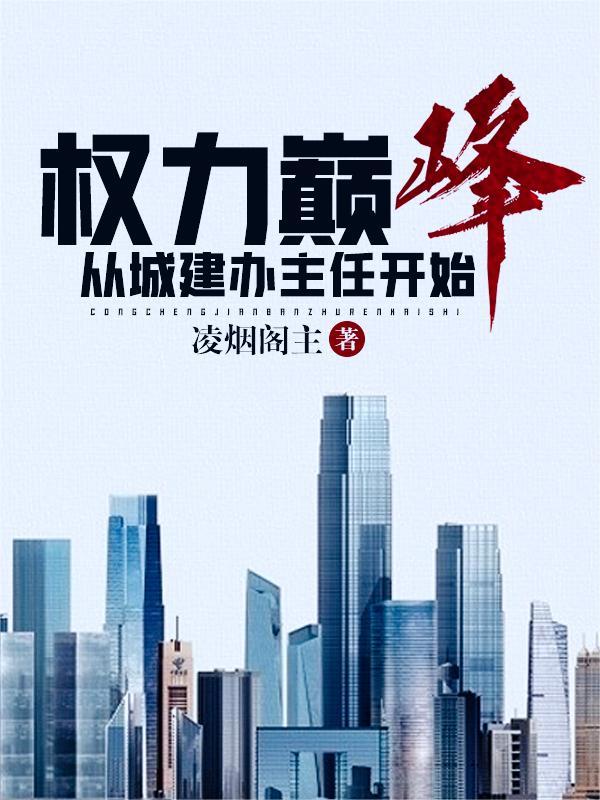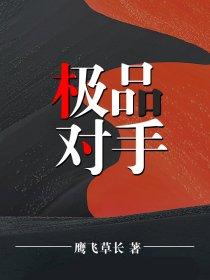旺仔小说网>离婚律师收了8000 > 他只是选择了忽略(第1页)
他只是选择了忽略(第1页)
记忆被拉回到半年前,2025年1月31日,年初三。
浦东新区的这套新公寓里,冬日稀薄的阳光透过落地窗,在地板上投下斜长的、温暖的光斑。空气中漂浮着旧书页特有的尘埃气息,混合着实木家具淡淡的木质香。李笑然独自坐在地板上,四周散落着十几个刚刚拆封的纸箱,像是一座座承载着过往的小小山丘。
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。奶油色的墙面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,书架上已经摆满了她和女儿的书籍,柔软的长毛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——这个完全按照她心意打造的空间,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一个单亲妈妈重新开始的决心和勇气。
三个月前,法律的解脱就已经到来。2024年11月14日,那纸调解书为那段令人疲惫的婚姻画上了句号。李笑然还记得那天走出法院时,深秋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在地上,形成斑驳的光影。她深吸一口气,空气中带着凉意,却感觉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。
但生活的琐碎剥离,往往比法律程序更加磨人。离婚后的日子并不轻松,尤其是还要照顾年幼的女儿。好在她有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,虽然收入不算丰厚,但足够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。更重要的是,她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,不必再看他人的脸色。
真正的扫尾工作是在十二月。前夫书院镇乡下老宅里,还堆着她少女时代的"遗迹":笨重的实木书架、一箱箱中学时代的课本和笔记、还有那些记载着青春心事的日记本。父亲在电话里劝她:"囡囡,那些破东西值几个钱?雇货拉拉从书院拉回来,运费都比东西贵!丢掉算了!你看看现在一个新书架才多少钱,何必费这个劲?"
父亲算的是经济账,一辈子精打细算的上海男人总是这样实在。但李笑然只是轻轻摇头,握着手机的指尖微微发白。
"爸,不是钱的事。"她的声音温和却坚定,透过电波传达到另一端,"那是我的人生。就算要丢,也得由我亲手丢,不能留在别人家里,成了碍眼的垃圾。"
她要收回的,是对自身历史的全部掌控权。这段婚姻已经让她失去了太多,这些承载着青春记忆的旧物,是她最后的底线。她很快在App上下单,支付了那笔在父亲看来"不值当"的运费,将老宅里最后的记忆也悉数搬回了新家。
此刻,新年伊始,她终于鼓起勇气开始整理这最后一批东西。午后的阳光很好,灰尘在光柱里轻轻飞舞,像是时光的颗粒,每一粒都承载着一段回忆。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标注着"书院老宅"的纸箱,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中学时代的笔记本。最下面压着一个边角已经磨损的牛皮纸文件袋,封口的棉线依旧规整地缠绕着,保持着十四年前的模样。
她的心跳忽然漏了一拍,指尖轻轻抚过那个熟悉的文件袋,仿佛触碰到了遥远的过去。
十四年了。
里面是那个名叫文吉的少年写给她的四封信,以及她自己写下却最终未能寄出的三封回信。这些年,她搬过几次家,从大学宿舍到单位附近租住的小屋,再到婚后的婆家,始终带着这个文件袋,像一个沉默的时光胶囊。她偶尔会翻开,但也仅仅是看看第一封信的开头,那些略显稚嫩却真诚的笔迹,便再也没有勇气读下去。连着自己那三封未寄出的信,她也从未有勇气拆开重读。
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她刚刚结束了一段复杂的关系,亲手装修安置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,她的内核从未如此强大和稳定。经历了婚姻的失败,反而让她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自己,有了足够的力量去直面那段被封存的青春。
她小心翼翼地解开棉线,动作轻柔得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。抽出里面的信笺时,纸张发出脆弱的声响,仿佛在抗议这突如其来的打扰。信纸已然泛黄,边缘有些脆化,但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可见。
她一封封地读着,时而因为信中稚嫩的话语而微笑,时而因为那份纯粹的真诚而眼眶微热。那个忧郁又才华横溢的市重点少年,那个在扣扣上彻夜长谈、相约共赏烟花的灵魂知己。。。。。。所有的记忆都变得无比鲜活,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读着读着,一个念头猝不及防地钻进心里:他现在,怎么样了?
一丝极其微弱的、连自己都觉得可笑的期待悄然滋生:他。。。。。。会不会还是单身?
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,就被她自行掐灭了。她不禁失笑,摇了摇头。文吉比她还大一岁,那样优秀的一个人,怎么可能不结婚生子?她到底在幻想什么?
这只是一次对老友的怀念。她只是想在这离异后第一个新年,给沉寂的生活投下一颗名为"回忆"的石子,听听回声,让日子有点微澜和期待。
她想起当年互寄礼物时留下的快递面单,她是个念旧的人,连这个都没丢。她从文件袋里翻找出来,单据上的字迹已有些模糊,但收件人那一栏的姓名"文吉"和那个手机号码,却还依稀可辨。
她试着拨打那个号码,指尖在屏幕上犹豫了片刻,还是按了下去。听筒里传来冰冷而机械的女声:"对不起,您所拨打的号码已暂停服务。。。。。。"
果然。十四年,足以让一切物是人非。她轻轻叹了口气,说不清是失望还是释然。
她登录了手机扣扣——那个熟悉的、他用了很多年的号码,头像灰着,显示不在线。也许过年忙吧。她在那几乎空白的对话栏里,敲下了新年问候:"很久没联系了,今天在整理搬家的物品时,发现了我们高三那年往来的信件,14年了,试着拨通了电话,已经暂停服务了,14年里我搬了这么多次家,这些信件一直都没丢,包括你送我的《小王子》的书籍,14年里偶尔也会向人提起你,今天想起你,给你发一句新年快乐,也不知道你何时能看到了。"
接着,她点开了扣扣邮箱,给那个同样隶属于这个扣扣号的邮箱地址,发送了一封内容一模一样的邮件。标题就叫:是我,14年前高三的笔友。
点击"发送"后,她看着邮件进入已发送列表,心里那点微弱的火苗似乎也随之熄灭了。她用的是自己常用的邮箱,但对方的扣扣和邮箱,对她而言都是沉睡已久的黑洞。爱回不回吧,她想着,这事就算了了。
她放下手机,将读过的信小心收好,放回那个牛皮纸袋里,仔细地重新系好棉线。然后起身,去厨房给女儿准备水果,不再回头看那个也许永远不会得到回复的邮箱。
窗外,上海的夜景开始璀璨起来,霓虹闪烁,车流如织。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与她此刻的宁静形成鲜明对比。她并不知道,这封她以为石沉大海的邮件,会在整整半年后一个令人烦闷的夏夜,得到一封炽热到反常的回信。
而她更不会料到,在这一切尘埃落定、彻底诀别之后,她会因为需要手机扫码登录电脑上的邮箱,再次点开那个熟悉的扣扣。那时她会清晰地看到,那个号码的登录状态几乎永远是【手机在线】或【电脑在线】。
那一刻,所有的疑点会瞬间串联成冰冷的真相:那个号称"不常用邮箱"、"半年后才偶然看到邮件"的男人,其实一直活跃在这个社交网络上。那个和他的微信ID(wenjiid)源于同根、几乎一模一样的扣扣邮箱,就是他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数字身份之一。
他看到了。他必然看到了。无论是1月31号当晚,还是之后的几天。他只是选择了忽略。
直到半年后,当他陷入所谓的中年危机,感到极度空虚和寂寞时,才想起翻出这封来自过去的、或许可以成为他"情绪急救包"的邮件,精心编织了一个"翻硕士论文才看到"的拙劣借口。
但此刻,2025年1月31日的李笑然,对此一无所知。她只是享受着这份尘埃落定后的宁静,以及独自归置旧山河的、完整的掌控感。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,她的人生,正在开启全新的篇章。那封寄往过去的邮件,如同投入深湖的一颗石子,在沉睡了整整半年后,才终于要激起一场她始料未及的波澜。
而这封邮件的涟漪,最终将她推向了那束,作为重逢礼物的粉玫瑰前,无处遁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