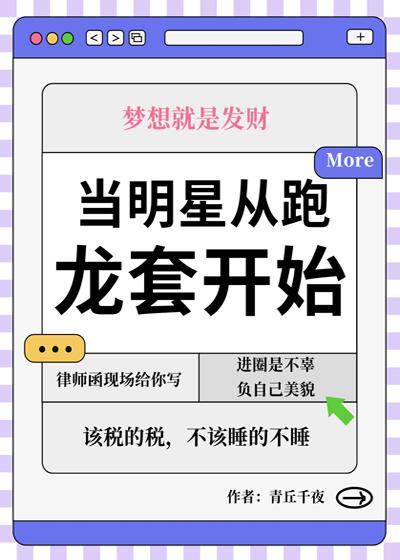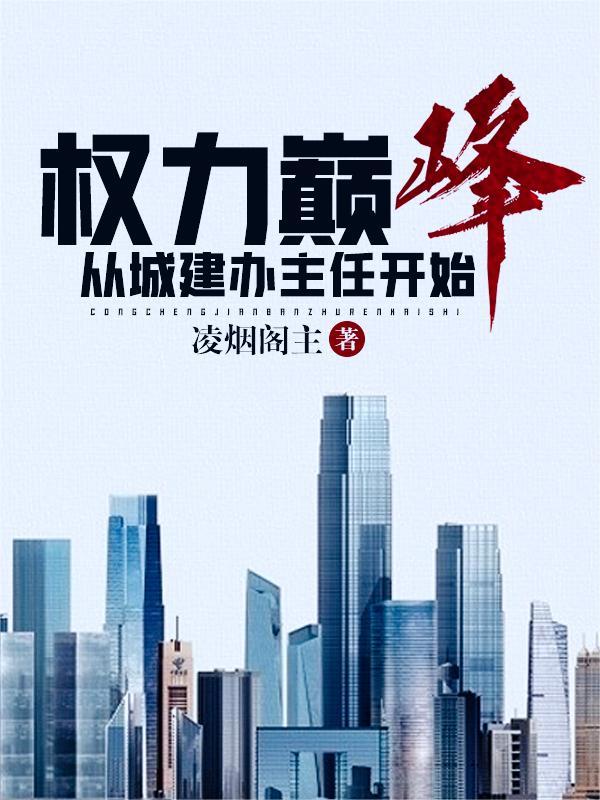旺仔小说网>微光与尘 > 余震(第1页)
余震(第1页)
【1】
夜雨未歇。
唐蓬莱从军监出来时,天已将明未明。灰色的雾裹着旧巷,电线在风中细微地晃动。军车停在路口,司机战战兢兢地下车撑伞,被他抬手制止。
“我自己来。”
雨水顺着帽檐滑落,他面色蜡白,军靴溅起的泥点在裤脚处凝成一层硬痂。那根拐杖握在掌心,木头早被水浸湿,沉甸甸的。
一路无声。雨点敲打着车窗,似在刻一场无形的悼念。唐蓬莱坐在后座,指节僵硬地扣着龙首,青筋暴起。风从车缝中灌进来,带着铁与血的味道。
车灯扫过唐家门前石狮,门口的仆人慌忙迎上,他只是微微抬手,未发一言。
他进门时,未脱外套。雨水滴了一地,留下一串晦暗的印迹。所有下人都屏声敛气,看着他径直上楼,背影挺直,却空。
那不是归家——
那像是一个战败的将军,拖着最后的旗帜,走进坟墓。
【2】
书房的灯影被风吹得摇晃。唐蓬莱脱下手套,手指在空气中微微发抖。
他将拐杖立在桌角,顺手取过布巾,开始一点一点擦。木纹早已被磨得光滑,他却仍在擦,像要把那根木头里的血迹全部抹去。
烛火映着他的侧脸,眼窝深陷。那神情,不是痛,而是彻底的空。
桌上散着几件旧物:一枚早已退色的军功章、一张合照——照片里,李常安笑得年轻而笃定,肩上披着同样式样的军袍。
唐蓬莱指尖在那张照片上停了很久,终于缓缓拿起,拇指在那张脸上轻轻摩挲。
那是民国二十六年,南京城已是山雨欲来。他刚从黄埔毕业,以中尉见习官的身份被派往一支即将开赴前线的部队。满腔都是救国图存的热血,也带着世家子弟特有的、不愿与“粗鄙丘八”为伍的孤傲。
部队在城外进行战前构筑工事的演练,一场急雨不期而至,将阵地化为一片泥沼。他为了示范一个战术动作,脚下打滑,整个人极其狼狈地摔倒在泥水里,崭新的军官制服瞬间糊满黄泥。
就在他耳根发热,准备迎接士兵们压抑的窃笑时,一个身影冒着雨跑了过来,二话不说就用力将他架起。
“长官,没摔坏吧?”那人瓮声瓮气地问,脸上淌着雨水,眼神里没有讨好,只有纯粹的担忧,“这烂泥地邪性,俺们庄稼人走着都费劲。”
这就是李常安。唐蓬莱当时又羞又恼,甩开他的手,冷声道:“管好你自己!”
李常安也不生气,只是憨憨地挠了挠头,然后从怀里掏出个被体温烘得半干、同样沾了点泥的馍,掰开一大半递过来:“长官,您晌午就没咋吃,空着肚子可没力气跟小鬼子干仗……俺娘说过,肚里有食,心里才不慌。”
后来他才知道,李常安老家在华北,家里的屋子、媳妇和娃,都没能逃过日本人的炮火,就剩一个老母亲逃难出来,不知所踪。他投军,不为功名,就为一句最朴素的念想:“打鬼子,给家里人报仇,让别的娃别再没娘。”
“俺没啥大本事,”李常安后来常这么说,“就有把子力气,不怕死。长官您有学问,指哪儿俺打哪儿,能多杀几个鬼子,就值了。”
火光忽闪,他放下照片,取出那支旧枪。金属在灯下泛着冷光,像被火焰映得发烫。他一颗颗地拆开,擦拭、组装,擦拭、再组装——
动作精准,近乎仪式。
擦到最后一颗螺丝,他的手忽然顿住。
那一刻,他听见窗外有雷声滚过。烛焰摇曳,他抬起手,一下掐灭了火。
黑暗中,他的呼吸微颤。
那不是哭,而是一种被压抑到极致的声音,像深井底的回音。
【3】
书房外,唐山海静静站着。
门缝下的光忽明忽暗,终于彻底熄灭。紧接着,是一阵短促的声响——像玻璃碎裂,又迅速归于寂静。
他指节抵在门框上,呼吸一滞,唇色苍白。
郭走丢不知何时走到他身后,她没出声,只是站在同一片阴影里,陪他一起听屋内的沉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