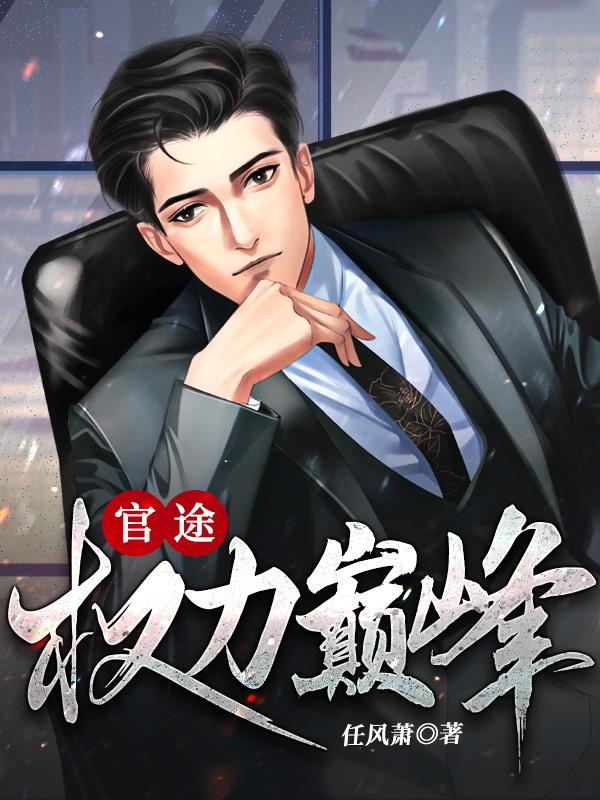旺仔小说网>食骨记火锅德化坪埔 > 泉州港鱼骨架粥船商志(第1页)
泉州港鱼骨架粥船商志(第1页)
一、港畔粥香,骨藏壮阔
南宋泉州港的清晨,总带着一股咸湿的海风气息。码头上桅杆林立,远洋商船的帆布在风中舒展,像一只只展翅的海鸟;搬运货物的脚夫们吆喝着号子,将丝绸、瓷器从船上卸下,又将香料、宝石装上船,脚步声与海浪声交织在一起,热闹而鲜活。在码头旁的巷口,有一家小小的粥铺,没有醒目的招牌,只在门口支着一口巨大的陶锅,锅里熬着的鱼骨架粥,香气混着海风,能飘出半条街——这就是林伯的粥铺。
林伯今年六十多岁,头发花白,却依旧精神矍铄,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粗布短衫,袖口挽到小臂,露出的手臂上布满了老茧,显然是常年与海打交道的模样。他手里握着一根长勺,正轻轻搅动着锅里的粥,眼神却望着码头方向,像是在等待着什么,又像是在回忆着什么。陶锅旁堆着几根巨大的鲨鱼骨,骨头表面泛着淡淡的光泽,显然是经过精心清洗和晾晒的。
陈墨背着装有《味魂录》的包袱,沿着码头的石板路慢慢行走。自离开临安后,他便一路南下,来到了泉州港——这座南宋最繁华的港口,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。这里的氛围与临安截然不同,少了几分水乡的温婉,多了几分海洋的壮阔,连食物的味道,都带着海风的咸润。他怀里的银汤勺,自记录下西湖蟹骨酥的食谱后,便又恢复了沉静,却在靠近林伯的粥铺时,突然轻轻颤动起来,勺身泛出一层淡淡的蓝色光晕,像极了深海的颜色,与之前遇到的淡青色、柔白色光晕都截然不同。
“老丈,来碗鱼骨架粥?”林伯看到陈墨,笑着招呼,声音带着几分沙哑,却格外有力,“咱这粥,用的是远洋商船带回的大鲨鱼骨,熬了整整一夜,鲜得很,还带着海风的味道,客官你尝尝?”
“劳烦林伯,一碗鱼骨架粥,多加些粥底。”陈墨走进粥铺,找了张靠门口的木桌坐下。粥铺不大,却收拾得干净,桌面上摆着一碟咸菜和一罐鱼露,墙角还堆着几个陶瓮,里面装着熬粥用的杂粮。
林伯应了声,转身从陶锅里舀了一碗粥,端到陈墨面前。粗瓷碗里,乳白色的粥底浓稠绵密,几块巨大的鲨鱼骨沉在碗底,粥面上飘着少许葱花,香气扑面而来,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海风咸润,让人瞬间想起辽阔的大海。
陈墨拿起勺子,舀了一勺粥送进嘴里——粥底软糯,带着杂粮的清香,鲨鱼骨熬出的鲜味融入粥中,鲜而不腥,还有一丝淡淡的咸,不是盐放多了的咸,而是海风特有的咸润,像站在船头,感受着大海的壮阔。可就在这时,那股咸润里,突然透出一丝未竟的遗憾,像壮志未酬的叹息,藏在粥的鲜香里,让人心里一沉。
陈墨下意识摸向怀里的银汤勺,指尖刚触到勺身,就感觉到一阵明显的颤动,紧接着,勺身泛出一层明亮的蓝色光晕,在勺面上映出一个模糊的身影。他屏住呼吸,仔细看向银汤勺——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,穿着一身深蓝色的锦缎长袍,腰间系着一条玉带,手里握着一卷图纸,正站在一艘商船的甲板上,对着身边的水手说着什么。男子面容刚毅,眉眼间与林伯有几分相似,他的目光望向远方的大海,眼神里满是坚定,像在守护着什么珍贵的东西。
“远航,这次出海,一定要注意安全,早去早回。”甲板下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,正是林伯的声音,只是比现在多了几分中气。
男子回头,笑着说:“爹,您放心,我走海上丝路这么多年,什么风浪没见过?等我回来,再给您带几根大鲨鱼骨,熬您最爱喝的粥。对了,这次船上的瓷器和丝绸,要是能顺利运到海外,换回来的药材,就能帮不少百姓治病了。”说着,他把手里的图纸小心翼翼地收好,转身登上了船舷,望着远方的大海,眼神里满是期待。
银汤勺的光晕慢慢暗下去,陈墨握着勺身的手却有些发紧。他抬头看向林伯,只见他正坐在灶台旁的小板凳上,手里摩挲着一根鲨鱼骨,眼眶微微泛红,像是在想什么心事。
“林伯,您这鱼骨架粥,熬得真是特别,带着大海的味道。”陈墨犹豫了一下,还是开口问道,“只是这粥里,似乎还藏着别的味道,像是……像是未完成的心愿。”
林伯身子一僵,缓缓抬起头,看向陈墨的眼神里带着几分惊讶,又有几分躲闪:“客官是个细心人……那是我儿远航的心愿。远航走了,可这粥里的味道,却像他还在一样。”
二、船商遗志,图藏深海
林伯的话,像一块石头投进陈墨心里,泛起层层涟漪。他看着林伯泛红的眼眶,轻声说:“林伯,要是您不介意,能不能跟我说说远航的事?”
林伯点了点头,拿起小板凳坐到陈墨对面,慢慢说起了远航的故事——远航是他唯一的儿子,从小就跟着他在船上长大,对大海有着深厚的感情。长大后,远航成了泉州港有名的船商,常年驾着商船走海上丝路,把大宋的丝绸、瓷器运往海外,再把海外的香料、药材运回来。他每次回来,都会给林伯带几根巨大的鲨鱼骨,说“这骨头熬粥香,还能让爹想起海上的风”。
“三年前的秋天,远航又一次出海。”林伯的声音带着哽咽,“那次船上装的,都是上好的丝绸和瓷器,还有一些官府托付的药材订单,说是要运往海外,换回来的药材能治疗地方上的瘟疫。可谁知道,船走到南海的时候,遇到了海盗。那些海盗凶残得很,不仅要抢货物,还要杀人灭口。远航为了保护船上的货物和水手,带着大家跟海盗搏斗,可海盗人多势众,最后……最后船被海盗凿沉了,远航他……他就再也没回来。”
林伯说着,从怀里掏出一个旧布包,打开布包,里面是一块深蓝色的锦缎碎片,上面还沾着些许海水的盐分:“这是远航衣服上的碎片,是后来水手逃回来时带回来的。他临死前,还在喊‘不能丢了大宋的东西’,还在惦记着那些要换药材的货物。”
陈墨看着那块锦缎碎片,心里满是敬佩——林远航不仅是个船商,更是个有家国情怀的义士,为了守护大宋的货物,为了能让百姓用上药材,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他想起银汤勺里林远航站在甲板上的身影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,又敬又叹:“林伯,远航大哥生前,有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东西?比如航海日志或者航线图之类的?”
林伯点了点头,眼神里露出几分遗憾:“远航每次出海,都会记录航线图,他说海上风浪大,好的航线图能让更多人安全出海。他还说,等他以后不跑船了,就把所有的航线图整理出来,交给船商公会,让大家都能用上。可谁知道,他还没来得及整理,就……”林伯的声音越来越轻,最后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“林伯,我或许能帮你找到航线图。”陈墨的眼神很坚定,“我这把银汤勺,能映出藏在食物里的魂灵。刚才我喝粥的时候,勺子里映出了远航大哥的身影,他手里拿着一卷图纸,或许就是航线图。说不定,银汤勺能帮我们找到航线图的下落。”
林伯愣了愣,随即眼里燃起一丝希望:“真……真的吗?你真的能找到远航的航线图?”
“我试试。”陈墨说着,拿起勺子,舀了一勺鱼骨架粥,靠近银汤勺,勺身再次泛起明亮的蓝色光晕,这次映出的画面更清晰了——林远航站在沉船的甲板上,手里紧紧握着一卷图纸,海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膝盖。他环顾四周,看到不远处有一块巨大的礁石,礁石下方有一个隐蔽的洞穴。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把图纸塞进一个防水的木盒里,然后将木盒抛进洞穴,嘴里还念叨着“爹,航线图……要交给公会……”。
陈墨赶紧把银汤勺里的画面告诉林伯,还凭着记忆,画出了礁石的大致模样和位置:“远航大哥把航线图藏在了南海的一块礁石洞穴里,那块礁石形状像一只展翅的海鸟,很好辨认。”
林伯激动得站了起来,双手微微颤抖:“是那块‘海鸟礁’!远航以前跟我说过,那块礁石附近海域平静,是个隐蔽的好地方。我这就去找船商公会,让他们派船去打捞!”
当天下午,林伯带着陈墨来到泉州港的船商公会。公会的会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子,名叫郑海,也是个老船商,与林远航相识多年。听完林伯和陈墨的讲述,郑海深受感动,当即决定派两艘快船,带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和潜水员,前往南海的“海鸟礁”打捞航线图。
“林伯,您放心,远航是我们泉州港的骄傲,他的心愿,我们一定帮他完成。”郑海拍着林伯的肩膀,语气坚定地说,“这航线图不仅是远航的心血,更是我们海上丝路的财富,有了它,以后大家出海会更安全,能让更多的货物顺利运到海外,也能换回更多的药材和物资,造福百姓。”
接下来的几天,陈墨和林伯每天都在码头等待消息。林伯每天都会熬一锅鱼骨架粥,送到码头,分给等待的水手和渔民,说“这是远航最爱喝的粥,喝了它,就能平安回来”。陈墨则在一旁帮忙,偶尔会拿出银汤勺,勺身泛出的蓝色光晕里,总能看到林远航站在礁石旁,守护着木盒的身影,像是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
第七天清晨,打捞的船队终于回来了。潜水员抱着一个防水木盒,快步走到林伯面前:“林伯,找到了!这就是在‘海鸟礁’洞穴里找到的木盒,里面真的有航线图!”
林伯颤抖着双手,打开木盒——里面整齐地叠放着十几张航线图,每张图纸上都详细标注了海上的航线、暗礁的位置、避风港的坐标,还有一些应对风浪的技巧,图纸的末尾,还写着“愿此图能护丝路平安”几个字,正是林远航的字迹。
“找到了……终于找到了……”林伯抱着航线图,眼泪掉了下来,声音里满是欣慰,“远航,你的心愿,爹帮你完成了。”
三、图传公会,魂释壮志